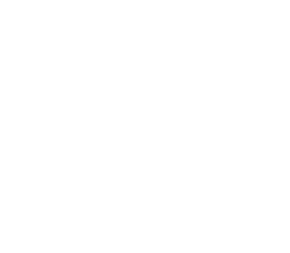在玄宗朝,佛教各教派虽然持续发展,但是由于玄宗本人对道教的强力推崇,与武后与中宗时期相比较,实际上是佛教发展的低谷期。同时,由于武后韦后多崇尚佛教,利用佛教危害李唐统治,玄宗在宫廷政变中成长起来,对佛教的积弊有清醒的认识。再加上道教被尊为国教,被认为是维系李唐王朝的正统,所以重新建立李姓皇权的统治,就需要多依靠道教,所以对佛教就多有限制。
开元初著名的宰相姚崇就强力反佛,为玄宗最初的宗教政策推波助澜。“先是,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符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上纳其言,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在临终之时更训诫家人,“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
在姚崇的推波助澜下,玄宗对佛教实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有许多诏令虽然名义上是佛道共禁,实际上针对佛教一家的可能性更大。开元二年下“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诏”、“禁百官与僧道往还诏”、“禁创造寺观诏”;开元十年下“禁僧道掩匿诏”;开元十二年“禁僧道不守戒律诏”;此外还有“禁坊市铸佛经诏”、“禁士女施钱佛寺诏”、“禁僧道敛财诏”、“括检僧尼诏”、“澄清佛寺诏”、“禁僧俗往还诏”、“流僧人怀照救”等等。开元初,玄宗励精图治,积极治理国政,所以起初对密宗僧人,包括对道士的推崇都建立在他们有助于解决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的基础上。但是,到后期“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产生了骄奢心理,怠于国政,对道术、法术等神异的东西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开元二十二年把自称有神仙之术的方士张果招入宫廷,恩礼甚厚。据《旧唐书·王玛传》记载“开元末,玄宗方尊道术,靡神不宗。”在《资治通鉴》中也记载着开元二十五年“时上颇好祀神鬼,故玛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上悦之以为侍御史,领祠祭使。屿祈祷或焚纸钱,类巫现。习礼者羞之。”开元二十九年,夜梦玄元皇帝,开始了对玄元皇帝的大力宣传,画玄元像,令诸州立开元观,自导或他演玄元皇帝降临的神话。对祥瑞的态度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玄宗早年励精图治,对吹嘘政治的祥瑞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开元三年下“祥瑞不须闻奏并申碟所司诏:至于嘉颖连理之祥,飞禽走兽之异,出于邦家,来献纲庭,虚美推助,非予所尚。岁宴奏陈于清庙,元正列上于大朝,探讨古今,亦无明据。”然而到了晚年,态度就截然不同,越来越向往样瑞的出现。天宝十载下“报中书门下大同殿钟鸣手诏:联斋心大同,缅睹真迹,岂精诚远感而休应荐臻!今九华之钟,三清彻响,声闻金石,气含虚无,是知紫衰之宫,云耕降集;青童之府,烟景来游,将合律于云傲,表同和于阴侧,灵仙坐接,福寿昭然.然若揭永惟嘉祥,良深庆慰。”正所谓上之所好,其下必甚。玄宗好神异,而使得诸人争相言符瑞,造假以求官职者不在少数,群臣更竞相表贺无虚日。朝廷上下掀起崇尚灵异的热潮。比如那王守礼对天气变化多敏感。“时积阴累日,守礼白于诸王曰:‘欲晴’。果晴。想阳涉旬,守礼曰:‘即雨’。果连澎。岐王等奏之,云:哥有术’。守礼曰:‘臣无术也。则天时以章怀迁滴,臣幽闭宫中十余年,每岁被救杖数顿,见瘫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闷,欲晴,即轻健,臣以此知之,非有术也。’”只要是稍微有点异常,就被视为有术之人,可见当时的猎奇思潮了。
除了在政治上为自己增添天命神授的神化色彩之外,玄宗在开元末年、天宝期间,随着年岁的增长,其生理和心理上都发生了变化。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就提出个人的宗教在发展中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其生理需求的理论。在开元末年,玄宗已过知天命的年龄。岁月的流逝和身体上的变化,与日益昌盛的国势形成对比,所以对长生的渴望就比年轻的时候更强烈些,自然注意长生术。况且道教信仰本身所宣扬的“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世间的个人可以脱胎换骨,直接超凡入仙,不必等死后灵魂超度。”这种优越性和简易性,可谓正合玄宗心意。所以哪怕是自称有长生术者,也可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恩宠,而不考虑情况是否属实。《新唐书·方伎传》载姜抚“自言通仙人不死术,隐居不出。开元末,太常卿韦绦祭名山,因访隐民,还白抚已数百岁。召至东都,舍集贤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发还鬓,则长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终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赐中朝老臣。因诏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筋上千万岁寿,帝悦,御花粤栖宴群臣,出藤百奋,遍赐之。摧抚银青光禄大夫,号冲和先生。抚又言:‘终南山有早藕,饵之延年。’状类葛粉,帝作汤饼赐大臣。右晓卫将军甘守诚能铭药石,曰:‘常春者,千岁蕊也。早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抚易名以神之。民间以酒渍藤,饮者多暴死。’乃止。抚内惭悸,请求药牢山,遂逃去。根据史实记载玄宗对医药有所研究,应该懂得最基本的常识,但是在长生问题上却完全相信一个道士的话,若非是狂热到了一定程度是不会如此这般的。
在密法中虽然没有象道教一样的养生术,但是能够通过修心是可以达到清静的目的,从而实现身心和谐,生命的长治久安。《大日经》中有对通过咒术实现成就一切的途径,“如咒术药力能造所造种种色像,惑自眼故。见希有事,展转相生往来十方。然彼非去非不去。何以故?本性净故。如是真言幻,持诵成就能生一切。况且在密法中,修行者个人可以与大日如来直接或间接的沟通,最后可以达到“体如虚空,不始不终,不垢不净,不边不中”的境界。“从这点上说,它同道教修炼神仙,与道合一的途径相类似,‘各自开拓致使长生不老的养生法’,是以磨灭生死界限来取得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统一。”密宗和道教的接近性,也为密宗在玄宗朝的流传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玄宗本人还持有本命信仰。本命亦称元命,或与行年相合而称年命,是一种星命信仰,以天人感应的观念为其文化背景,把自身的命理与星辰相联系。《唐会要》卷八记载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封泰山事云:“有雄野鸡飞入斋宫,驯而不去,久之,飞入仗卫。忽不见,那王守礼贺曰:‘圣诞酉年,鸡主放酉。斯盖王道遐被,天命休祯,臣请宣付史官,以彰灵既。’”④在《旧唐书·礼仪志》记载“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封华岳神为金天王”。更有甚者,玄宗还利用本命相生相克的理念以企图解决政治上的事情。《旧唐书咬禄山传》载“帝登勤政楼,握坐之左张金鸡大障,前置特榻,诏禄山坐,袁其握,以示尊宠。太子谏曰:‘自古握坐非人臣当得,陛下宠禄山过甚,必骄。’帝曰: ‘胡有异相,我欲厌之。”,(此“厌”即为“厌胜”,是古代的一种抑制他人命运的迷信之法。)安禄山的本命年为癸卯,卯为木,玄宗的本命酉为金,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金克木,那么玄宗用金鸡障厌胜安禄山,想要藉借本命上克制,消除政治上的危机。这种利用人力之外的力量服务于政治,与借助密法消除灾难的思路是一致的。然而本命信仰与密宗的关系十分密切的。“本命禁忌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但其说在唐宋之时广为流行,这主要应与佛教势力主要是密宗的一度兴盛有关。”北斗七星是佛教密宗重视的星辰,金刚智译《北斗七星念诵仪轨》,不空译《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一行撰写《北斗七星护摩法》等。不空译的《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金刚经瑜伽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轨经》等等及其唐代青龙寺沙门法全集《供养护世八天法》,一行撰的《宿耀仪轨》、《梵天火罗九暇》中,也都有类似的本命星受到冲犯将会发生灾难的说法。所以,唐玄宗其人有崇异之好,而密法中又多存在这神奇之术,就难怪玄宗对密宗僧人的重视了。